与卓越的法学家相遇共感
《遇见法学家:西方法哲学简史》读后
2024-10-17 15:20:38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本书的立意旨在从过度技术化的法学研究氛围当中挣脱出来,重现法律思考曾经有过的论题广度和思辨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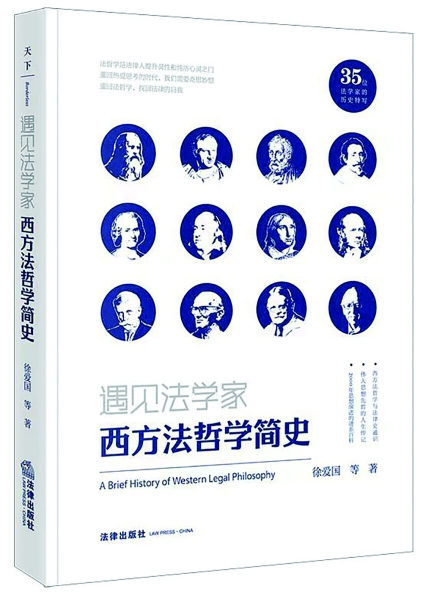
■《遇见法学家:西方法哲学简史》
主编:徐爱国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杨天江
法学家是研究和传授法学知识的人,法哲学则是对法律和法律制度所进行的一般性哲学分析。前者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共和晚期即已批量出现,后者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系统化于近代,但其萌芽却可远溯古代哲学家对法律与正义、道德和社会秩序关系的沉思。其间巨人频现,宏论绵延。
因此,无论是撰写一部法学家通论,还是出版一本法哲学专著似乎都难以命名,因为读者已对那些公认伟大的法学家及其箴言不再陌生,任何试图别出心裁的标题设计最终可能都不免落入俗套。然而,新近出版的由北京大学徐爱国教授领衔打造的《遇见法学家:西方法哲学简史》却迎难而进,提供了一个浓缩古今西方法学家精神世界的法哲学谱系。
本书的立意旨在从过度技术化的法学研究氛围当中挣脱出来,重现法律思考曾经有过的论题广度和思辨深度;在撰稿人的搭配上,则尽择受过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法哲学训练并仍在从事相关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一线教师,他们不仅了解法学家,而且了解读者可能在哪个地方误解了法学家;最终成果既适合初学者进行分析阅读,也欢迎谙熟者采取主题阅读,还鼓励爱好者选择检视阅读,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融汇之作
目前在法学家传记和法哲学教程这两个领域都有相当出色的译著出版。笔者各举两例:法学家方面,约翰·麦克唐奈和爱德华·曼森主编,由何勤华、屈文生和陈融等人翻译的《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记录世界法学史上最为著名的26位法学家的生平、代表性著作、法律思想、法学研究成就;格尔德·克莱因海尔和扬·施罗德教授主编,由许兰翻译的《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以德意志法学为主线,详细介绍了九百年来德国及欧洲的法学家及其学术贡献,对德意志法学及其对欧洲法学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梳理。法哲学方面,博登海默撰写,邓正来翻译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横跨法理学和西方法律思想史两个学科,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学界了解西方法学流派和思想演进的重要渠道;韦恩·莫里森写作,由李桂林、李清伟、侯健和郑云瑞翻译的《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采用批判反思的方法追溯和细查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法哲学观点,笔触犀利,读者纷至,一时纸贵。
无疑,以上作品是国内研究者从学生阶段过渡到教师身份必定涉猎过的重要文献,事实上它们也确实担得起这份历史使命。然而,从各个方面来看,《遇见法学家:西方法哲学简史》显然都未奉以上作品为圭臬,更没有打算以此限定自身的体例和内容。
首先,本书在法哲学人物的选取上视野更为宽广,35位或详或略、或集中或分散地探讨过法律主题的思想家和法学家陆续出场,全景敞视般地展示其人生际遇、鲜活个性、学术生涯以及代表性学说。正如主编徐爱国教授所讲到的,本书呈现了法哲学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幼年的法哲学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学混合在一起,青年的法哲学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和各自的流派,壮年的法哲学则回复到各自为政、自成一体的乌托邦与异托邦,至于老年的法哲学,现在尚不能预测和描述,也许是最后的死亡与重生。
其次,作为一部采众人之长、集各家之智的结晶之作,本书并未设定严格的哲学立场,不像博登海默那样试图调和分析法理学和价值法哲学,并以折衷的立场去应用法哲学;也不像莫里森那般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开篇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设置问题,随后尝试在传统与当代状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更不会像他那样以哈特之非验证奥斯丁之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更是一部融汇法哲学观点和命题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作品。
如何选取“历史的经纬”
虽说20世纪60年代之后,经过哈特的“抢救”,法哲学似乎又恢复了一些生机,至少在英语世界如此。但是,已过壮年的法哲学颓势尽显似乎不可避免,相形之下法律思想史却还在延续。因为法律思想还在不断更新,法学家还在不断涌现,他们可能会舍弃一部分哲学思考而去拥抱更加现实的问题,但只要他们还在工作,还在不断发挥作用,历史就还将展开。
法律思想史的书写离不开那些创造了思想历史的人物及作为其精神世界外化的著作,这些人物和著作就成了我们还原、加工甚至再造历史的依托。然而,究竟应当选取哪些人物和著作作为历史的经纬却是一个须细细思量的问题,即便这里所要绘制的不过是一部“简史”。从最远端的柏拉图到依然健在的波斯纳,时间跨度足有2300多年之久,其中有功于人类法律思想宝库者难以计数。
而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法律制度的缔造者,每种语言都不乏出类拔萃的代表作。比如,德国人书写法哲学可能会看重康德和黑格尔,法国人思考法哲学可能会从笛卡尔和卢梭那里汲取灵感,而英美世界的法哲学无疑会在从奥斯丁到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和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上停留许久。
但无论是哪国人,以何种语言书写,古希腊人的贡献,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无法回避。罗马人究竟是怎样把希腊哲学观念融入法律之中的尚存争论,但西塞罗无疑是柏拉图思想的传播者,而罗马法学家在组织自己的材料时肯定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法。其中,乌尔比安的学说尤具有代表性,毕竟他占据了《学说汇纂》近三分之一的分量。
从古希腊哲学到罗马法学的转化实际上是西方法律思想的一次“科学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材料来自罗马,但组织它的方法却是古希腊的。接下来的发展再次见证了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角力,前者以奥古斯丁为代表,后者则完美地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身上。
实际上,这两种思潮在思想史上一直复现,不过奥古斯丁主义并未在法律思想史上产生影响,而托马斯主义则历经晚期经院派到20世纪的雅克·马里旦直至在约翰·菲尼斯的著作中都一直保持着活力。神学理论体系首先遭遇的是文艺复兴的拷问,衰退中的经院哲学无法抵御对哲学解放的渴望,于是要么重回古希腊思想要么诉诸科学新发现成为当时的选项。格劳秀斯消解了永恒法,只在正确理性中寻找自然法的根据,这代表着真正现代法律思想的开端。他去世不久之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使欧洲从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和帝国政治过渡到以国家为单位的基本框架。
写作是一个“相遇”的过程
而从哲学角度来看,培根、笛卡尔和霍布斯的相继出现击溃了整个古希腊思想体系,现代思想秩序最终形成。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了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对作为现代国家基础条件的财产权、权利分立和社会契约等的思考。同一时期普芬道夫的理论则是霍布斯理论的德国回响,因其对国际法和美洲革命的潜在影响而变得重要。美洲革命是18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是旗帜性人物,同时代的亚当·斯密则是苏格兰启蒙的代表之一,深刻影响了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18世纪至19世纪,边沁是启蒙哲学的支持者,也是希望重构法哲学基础理论的革新者,他成为了奥斯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哈特和拉兹等法律实证主义学派的鼻祖。而萨维尼和梅因的历史主义则可视为对这种实证主义思潮的反动。20世纪之后法哲学发展基本上可以用“实证主义 其他”概括,“其他”包括了实用主义法学、法律社会学、新自然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等。这一时期司法判例、法官角色和法治等成为了法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
尽管本书到波斯纳戛然而止,但哲学家的事业未竟,思想史仍然待续。写作是一个“相遇”的过程,首先是创作者“遇见”法学家,接着让各个不同时期的法学家“会遇”,最后期待读者“遭遇”他们的思想。正如当代著名艺术家、哲学家布拉查·艾丁格在探讨主体性时所尝试提出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认知或情感上的外部关系,而是一种共感关系,是一种在与他者相遇时共同参与、共存和相互转化的过程。想必读者籍由与这本书的偶遇,也能与那些卓越的法学家共感。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责编:尹丽